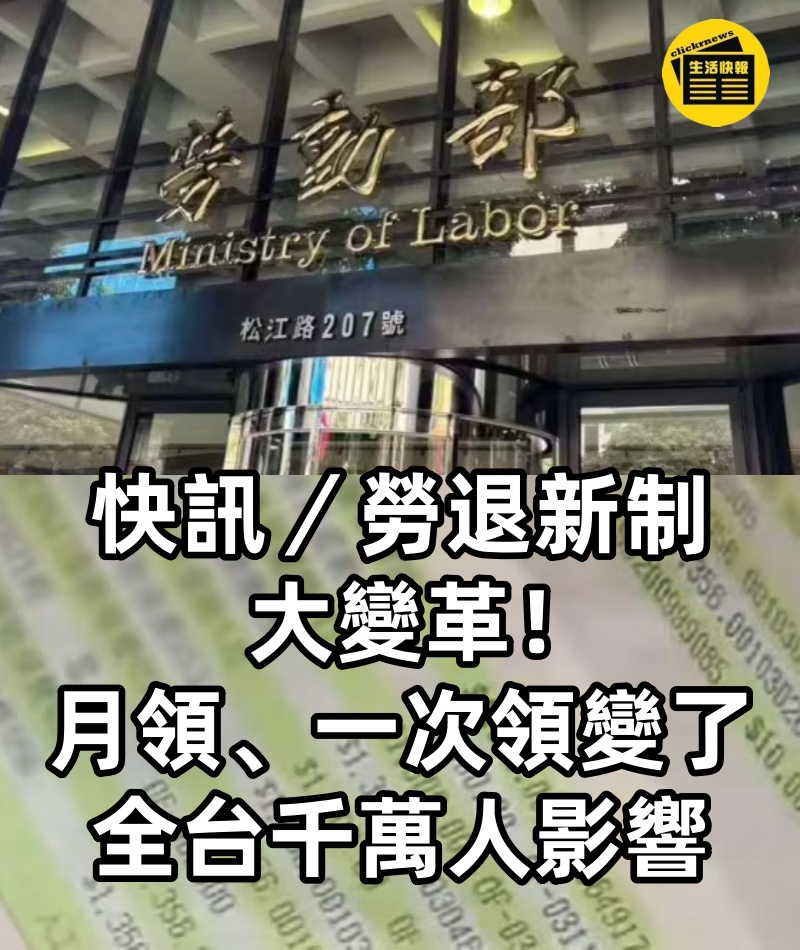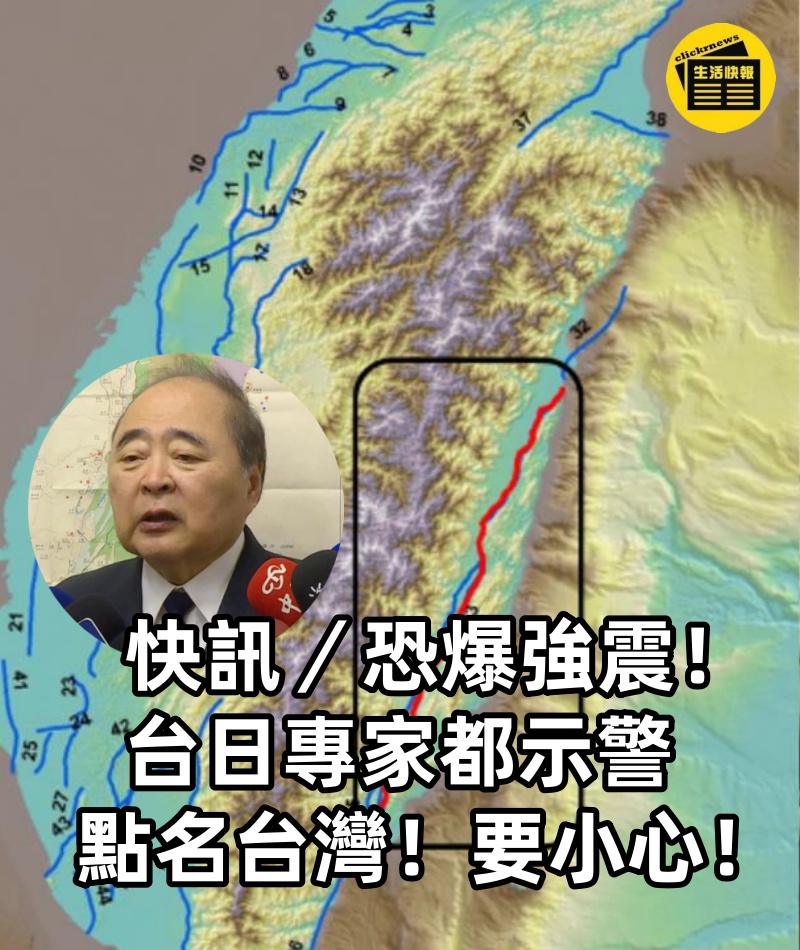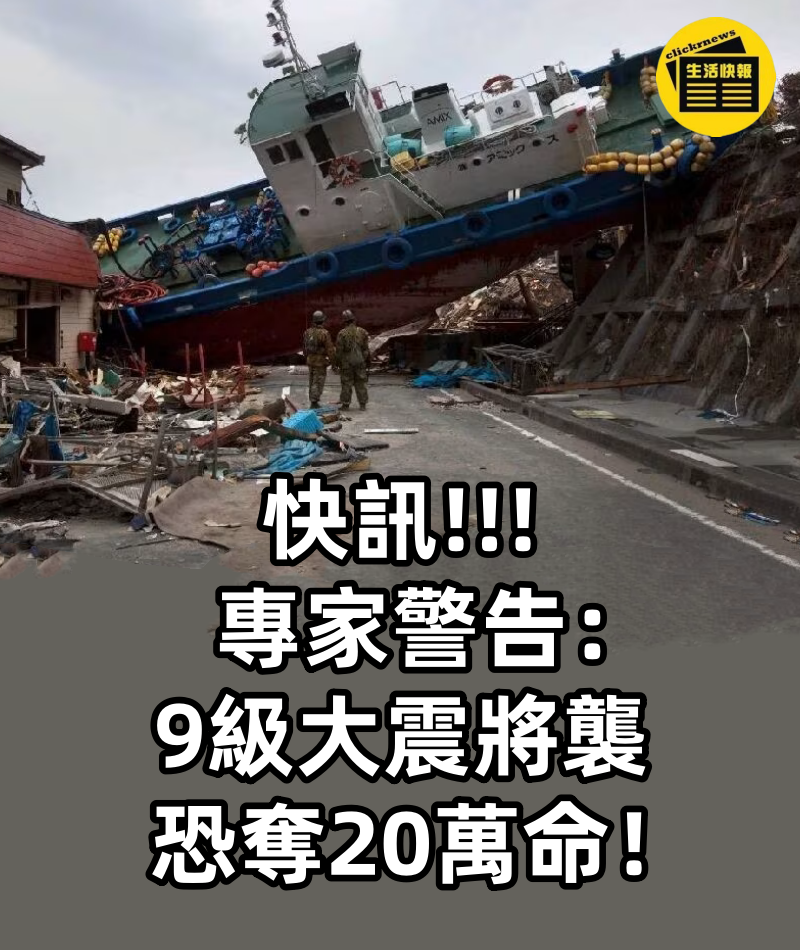這個武將熬死了秦始皇,熬死了劉邦,熬死自己兒子,最終熬成皇帝

他兵分三路,緩進急打,同時派使者撫慰民心,很快便平定兩郡,統一嶺南。

2 / 3
這時的趙佗,已經不再是秦朝的小官了。
他在番禺築起新都,設立王宮、百官、衙署,自稱「南越武王」,正式建國。
他的稱王並未張揚,卻非常明確,他沒有自號「皇帝」,也沒有頒布年號,而是取了一種亦忠亦叛的模糊姿態。
對外,他依舊尊稱中原王朝為「天子」,但在嶺南,他是不可違抗的最高統治者。
嶺南自古蠻荒,但在趙佗手中,卻漸漸成了一個「自留地」。
與漢朝鬥智斗勇
中原大地終於在連年戰亂之後迎來了一個喘息的間隙。
項羽自刎烏江,劉邦登基稱帝,漢立國。
這一年,趙佗已是嶺南之王,百越歸心。
這雖名為「南越」,但疆域之廣、民眾之眾、財富之豐,足以讓任何一個帝王起貪念。
於是,公元前196年,劉邦派出了最會說話的人,陸賈,肩負著「勸趙佗歸漢」的重任,手持詔書、玉印,一路南下。
趙佗對此並不急於回應,陸賈到了番禺,足足等了幾個月,才被允許覲見。
他進入王宮,只見趙佗身著越人裝束,滿頭鬢髮高束,坐姿隨意,稱呼自己為「蠻夷大長老」。
這一幕,簡直像是在考驗一個使者的耐性和格局。
陸賈是個聰明人,他行了個禮,說:
「大王之地,海天浩渺,然稱王於嶺南,不若封侯於天下。」
他言語溫潤,卻話中有鋒,既提醒趙佗歸漢的好處,也暗藏帝王之威。
趙佗聽罷一笑,道:
「吾居蠻夷久矣,失禮義,然吾不與中國爭,不代表吾不能爭。」
他態度表露得清清楚楚,我可以歸漢,但你們最好別把我當成軟柿子。
最終,在權衡再三之後,趙佗接受了劉邦的冊封,稱「南越王」,向漢廷稱臣納貢。
這是一次策略性的俯首,此時的南越雖穩固,但尚未完全脫胎成一個能與漢朝匹敵的王國。
歸漢,換來的是時間,是穩定,是外部的緩衝,是中原強敵對他的暫時「放手」。
但這樣的默契沒有持續太久。
劉邦死後,呂后臨朝,這位狠辣果決的皇太后,對趙佗並無好感,或許是因為他自稱「蠻夷」,也或許是因為她容不下一個強勢的藩王遠據南疆。
她下令禁絕南越鐵器貿易,扣押使者,還擅自將原本屬南越的桂林、象郡劃歸長沙國。
趙佗怒不可遏,他本就是兵出身,不似那些諸侯王只會在朝堂上拱手作揖。
這一次如果再忍,失的就是根基和未來。
於是,趙佗反其道而行之,以「南越武帝」之號登基稱帝,斷絕與漢朝的官方來往。
同時,派兵襲擾長沙國邊境,將呂后扶持的漢軍打得節節敗退。
他的軍隊不多,但熟悉地形,兵精將勇,中原士卒南下,水土不服,未戰先病,尚未越嶺便已潰敗。
這場對抗,使趙佗在嶺南的威信空前高漲,周邊部落紛紛來附,趙佗不再只是嶺南之王,而是整個南方世界的共主。
接著,呂后病逝,文帝劉恆登基,在得知趙佗之事後,沒有一味強硬,而是選擇修舊好。
他命人重修趙佗祖墳,派人年年祭祀,厚待趙家在中原的親族,又一次派陸賈出使南越。
這一次,陸賈帶來的,不僅是詔書與禮品,還有一封文帝親筆信。
信中語氣柔和,情意真摯,稱趙佗為「舊臣宿將」,盼其歸順,共襄太平。
趙佗看完書信,沉默良久,長嘆一聲:「天命如此。」
他再次歸漢,去帝號,復稱「南越王」,在禮儀上重新歸入漢廷體系。
但這一次,趙佗並沒有交出實權。
他對漢朝稱臣納貢,年年派人赴長安朝拜,但在南越國內,他依舊以皇帝禮儀治政,發布詔書、任命官吏、徵稅治民,一切如常。
這是他最擅長的平衡術,對外表忠,對內獨裁。
稱王稱帝之間,他幾進幾退,不為虛名所動,也不為一時之氣所困。

3 / 3
他要的是一個長久的南越,一個在大風中不倒的王朝。
趙佗活得太久,經歷太多,而他始終如磐石般穩固,憑著一顆擅謀的心,在夾縫中開疆拓土,在天命下爭得一寸自由。
最後孤獨
嶺南在趙佗的經營下,早已不是當初的樣子。
這個他用半生征戰、半生經營的地方,終於如他所願,從蠻荒之地走進文明的門檻,漢越一家,血脈交融。
而他,也從一個北方小將,活成了這片土地的「始祖」。
可再強的王,也無法抗衡時間的鐵律。
趙佗逐漸老了,從最初策馬橫戈,到後來拄杖巡視,他的身影變得佝僂,鬢髮早已斑白。
但他的眼神依舊炯炯,政事從不放手。
他信不過旁人,也不願旁人攪亂他一生打下的基業。
他唯一的兒子,是他寄託最多的希望,從小就帶在身邊,親自教授兵法禮制、民生政理。
但命運殘酷,趙佗年逾九十之時,白髮人送黑髮人,親眼看著愛子病亡。
孫子趙胡被立為太子,那是趙佗人生的無奈。
孫子並無太大雄略,但已是唯一血脈。
他開始放權,卻依舊把控著朝綱的脈絡,教導趙胡要「忍、穩、和、遠」,可他也明白,這一代之後,南越可能撐不住漢朝如山的壓力。
公元前137年,趙佗終於走完了他百年之路。
據史書記載,他享年一百餘歲,在那個人均四五十歲就算長壽的年代,簡直是活成了神話。
他死得安詳,卻也孤獨,周圍親故皆早亡,手中權柄也無人可托。
他的一生,熬過了秦始皇、熬過了劉邦、熬過了呂后,甚至熬過了自己的兒子,卻終究熬不過時間。